|
乾县二中,我人生真正起步的第一块基石,其情其景,其人其事,至今历历在目,铭心刻骨。
四十年前,我有幸从乾县最偏远的关头高中,神差鬼使,来到想都不敢想的乾县二中任教。
说来有点话长。我一九六五年,作为万千吃不饱穿不暖的农民子弟,考入乾县一中。一场突如其来的“文革“,打断了我梦寐以求且十拿九稳的大学梦。
狼狈不堪地回到生我养我的村庄。
泣血叩首,谢天谢地,多亏我在一中读书时的陈书记。是他,在我潦倒无依时,出于爱人惜才之心,力排众议,使这个富农出身的孩子有了一线生机,有了一点微薄的用武之地一一我成了全公社唯一的“黑五类“子女站上讲台的人民教师。
感恩之余,在那不堪往顾的岁月里,我没有随波逐流,没有放纵自任,競競业业对待每一节课,认真负责看待每一个学生。在当年的暑期培训中,我作为教师的老师,常常彻夜不眠,准备讲稿,赢得了一致认可,县教育局派驻的巡视组也给予充分肯定,大加褒扬。
在这样的气场和氛围中,加上十年浩劫人才断层的客观条件,我才能在没有任何社会背景的条件下调入县城,来到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乾县城关第二中学。
作为农民子弟,感同身受,我深知我的学生求学之不易,生计之艰宭,家庭之期待。在尽心努力(另叙)的同时,我把最大的精力投入到对学生的要求,与家长的沟通上。每到周日(那时还是每周六天工作),我总要骑上自己的那辆只有铃不响,其他都在响的破旧不堪的自行车,到我认为需要家访的孩子家里,或盘腿上炕,或院里拉呱。没有茶水,更没有饭菜,唯有一双双充满期待的目光。到现在仍然记得,学生张养文那瘦骨嶙峋的母亲,挣扎着从高高吊起的竹笼里,拿出她认为最珍贵的礼品一一自家院里长出,放了多久的大杏!尽管表皮已发黑,但吃在口里,那滋味却饱含着一位长者的深情寄托,无论怎么形容,怎么品味,都难以言表!
承受着这样的翘首以盼,面对着渴望跳出农门的孩子,我怎能不心潮汹涌,我怎能残忍撒手!
为了孩子,为了一个家庭的寄托和未来,唯有教者先知敢拼才能对得住自己的良知!唯有教者把学生家长看成是自己的亲人,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子弟,为他们义无反顾,倾注自己全部感情,才无愧于一名合格教师的职业良心。
我尽己所学,全力以赴,丝毫不敢懈怠。对学生,我穷尽力心,甚至可以说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粗言相向平常事,拳杖交加时常有。这些琐细常事,容当后叙。只讲印象较深,至今仍难以释怀的几件小事。
一九八一年,是我教毕业班的第一年。当时二中的高考业绩,只有用“可堪回首“四个字概括。一年包括高中专在内,全校能考上三十名学生就皆大欢喜。记得那年七月底的一天,连阴大雨,街道泥泞不堪,路人小心翼翼,缓步绕行。下午,学校宋书记破例找到我,拿出一纸文书,说是邮局刚送来的。我捧手一看,是学生窦富国的录取体检通知,因为他报考军校要提前录取,要求两天内必须去指定医院体检,合格后才能录取。书记可能也感到时间紧迫,又有大雨泥路阻隔,才来找我商量。我看过通知,又看了看窗外瓢泼雨势,没有一点犹豫,“我去“!说着,就披了一条包袱布,双手推起脚踏只剩一根钢条的“红旗“自行车,不管不顾地冲向雨雾。
出南门柏油路,不一会就到南村桥头。过羊毛湾干渠,我登时傻眼。脚下往前,都是土路,坎坷泥泞,我一双低腰胶鞋根本没用,很快就被泥水灌满,举步艰难之际,看见路边的兽医站,抖抖身上雨水,蹦跶腿脚污泥,推车走进院子。一位约摸五十岁左右的汉子从屋里出来,他看到大雨中的我,顿时吃惊,忙问有啥紧事等不到雨住再出来。我委婉地说了原由。只见他面露惊异谦恭神色,连说老师好心肠,老师好辛苦,老师不容易。叮嘱我前面路自行车也推不动,只能步行。又说我低腰胶鞋不行,让我稍等。不一会,他提了一双高及膝盖的胶鞋给我换上,说离学生所在村还五里路,要我小心路滑。我来不及感激这位好心长者,只想着尽快赶往学生家。草草道谢后,又深一脚浅一脚艰难慢行。
凭记忆,我找到学生所在村,几番打问,才找到他家。传统农家的间半庄子,一溜厦屋高低排开,一看就知道是分几次盖的。富国的父亲我在县城见过几回,但眼前的我,他似乎不认识,等我拉下早已淋透的床单,他才惊呼“,王老师,是你!“等到我把通知交他仔细看后,我心颤了。他双手抖动,泪眼婆娑。几次张口,欲言又止。后来只挤出了几个字:“娃总算考上了,老师你太好了!“那时,我也沉浸在一种无以言表的心绪场景中。是啊,还有什么能比一个教师看到自己的学生跃出农门的现实更打动心魂的呢?还有什么能使一个农家看到孩子通过努力,免除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宿命来体现一个教师的价值呢。
于是,我抹了一把满和雨水泪水的脸,带着难言的满足和无上的自豪,在全家人喋喋不休的感激中,在大雨和泥泞里,踏上回校的路。
一九八O年,又是一个暑假结束,新学年开始的日子。一天下午,我刚用过简单的晚餐,在房间看书,学生祝转民推门进来,满脸愁色,直挺挺地站着。我忙问:“有事吗?“他犹豫着,忐忑不安又局促急迫。面对聪颖优秀却无奈落榜的他,我大声说,“有话只管讲,老师会支持你的“。断断续续,他讲述了自己的为难和酸楚。孩子命苦,幼时丧父,和母亲兄长相依为命,苦煎苦熬,举全家之力,好不容易念到高中,按平时的学业和成绩,一榜高中板上钉钉,没想到那时高考百中选一,稍有差池,以三两分的差距名落孙山。他没灰心,想着复读重来,但母亲有心无力,哥嫂虽然吃的公家饭,但收入微薄,养老顾小,捉襟见肘,决定让他回村务农。听完他的诉说,我震撼痛惜,再也静不下心。当时就说,我们一起去邮政局。夜色渐深,在他哥嫂居住的简易三层楼下,尽管因临时施工挖断了路,我还是亳不犹豫,戴着近两千度的近视镜,爬着简易铁梯,摸进他哥的家。一进门,小俩口估计也能猜出我的意图,就是回避正题,只聊些柴米油盐的琐事。我觉得不能这么干耗着,就直奔主题,开诚布公,叙说学生的优秀,并一再打包票,声言下次他一定能考个好学校。没想到那小俩口,互相对看着,没态度,不吱声。我急了,单刀直入,说我这个学生,不补习太可惜,会耽误他一辈子的。还打肿脸装胖子,说我知道你们家有困难,我先垫钱供着,以后再说。
见我说这份上,他们脸红了。互相又交換几番眼神,男的终于开口了:“咱的兄弟,咋好意思让老师破费。好,我们再供他一年“。一句话,云开雾散。我和转民兴匆匆下楼。
孩子刻苦争气。第二年,他如愿考上西安交通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航天卫星测试计算,成为国内高端科技的领军人物。
三年前,他携带妻子和男孩到我家,忆当年事,欷欷再三,也谈到他们兄弟至今还常常念及的这宗往事,都觉得多亏王老师。对我而言,象这样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绝对不是孤例。春蚕蜡烛,教师的本能,也是天职。尽心了就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对学生,对社会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为师如此,我心足矣。
还有,在一九八二年,我教高中毕业班的第二个年头。那年代,因为考生数量多,录取人数少,为了减轻高考负担,降低考试成本,实行考前初试制度。先粗筛一次,优者再上正规考场。那年初试刚过,我阅完考卷,难得闲暇,一上街随意散步。在西大街路北,一群人正起劲地打土墙。我一抬头,看到墙头提铁锤子三个人中,有学生王文利。我立时怒火中烧,踅足大叫他的名字。孩子一时慌了神,打墙的一干人众也不明就理,直楞楞地看着我。我咆哮着:“王文利,你给我下来”。他乖乖地丢开锤子跳下来,不知所措地沾在我面前。我不容置辩地大喝,“跟我走“!径直领他到家。
他父亲约长我十岁。我严正地说,文利是你的孩子,但还是我的学生。预选完了绝不是高考结束,他有上榜的条件,但是不能放任。你要明白全省考生一分差距往往有成百上千人。他应该在家复习攻读,而不能再干与学习无关的事。看着老头子难堪的面色,我又调侃了几句,说是我老家的土墙早有破损倒塌,他考完试如有可能,也可以在那里一显身手。文利的父亲听了这番话,紧紧握住我的手,一再表示谢意,保证把孩子管好,抓紧最后冲刺。后来,学生如愿考入北京化工大学,先留校任教,后下海经商,成为国外大品牌的国内总代理,生意风生水起,对国家的贡献得到官方的认可。
人梯,就体现在教者对每一节课的认真负责上,对日常点点滴滴的精心顾盼间,对学生一时一事的关心引导中,尤其是关键时节一切以学生为重的勇往直前。这大概就是乾县二中给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我对做一名称职教师的一点启示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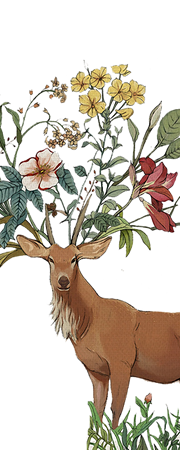








 陕公网安备 61040202000199号
陕公网安备 61040202000199号